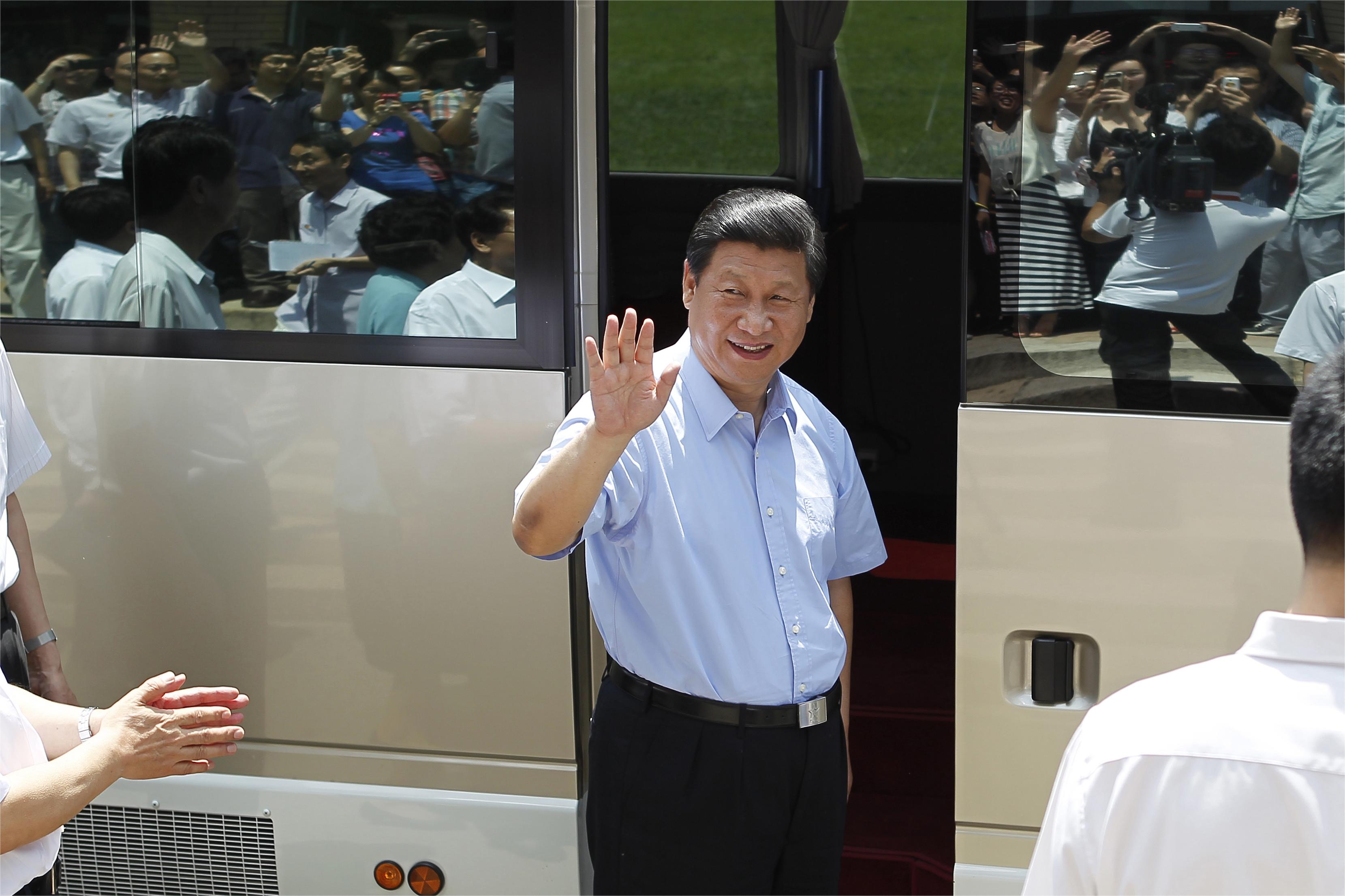在威尼斯住下去

1 一粒盐找到它的海
威尼斯岛卡那雷乔区,在这里我要住半载,一年,乃至更多,恐怕一住就是一年加半载也不止了。在整个威尼斯主岛上最安静的地方之一,感觉自己像是被世界忘掉了。被忘掉是值得洋洋得意的。
这种感觉就像一粒盐找到了它的海。即便是在邮局排了一上午队后办事员过来客气而坚决地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到这儿就下班了,您明天再来吧,即便是赶时间去多所多罗拿东西却怎么也到达不了钻进的每一条巷子都像是死胡同地图导航全失灵,即便是口罩把雾水裹在镜片上,眼睛也被熏得发酸——更可惜的是,口罩还挡住了满街漂亮男孩女孩的脸蛋,即便那些砖墙又老又发霉又潮湿泛灰,我还是无法拒绝地迅速爱上了这里。
威尼斯一直还是威尼斯,以它自己的方式中世纪了、文艺复兴了、现代又后现代着。人们经过它,都看到它的浮华热闹—— 来 之前,有个中国朋友和我说,威尼斯被温州移民毁了!事实证明,旅游业的轰轰烈烈全部倒戈,投机商人落荒而逃。而威尼斯一如既往地在这里,即便每天下沉几毫米,也气定神闲地如过往600年那样似乎要永远停泊下去。
阴雨天的威尼斯是小令,适合倚在窗前听,而朗朗晴空下她就成了磅礴汉赋,要亲自去云上踏了。虽然没有平时如织的游人,大运河上依然各式船来往如梭。游船都停在S. Marta的泊船场,在桥底下生起锈来。偶尔几艘贡多拉,一半是给近道儿而来的情侣,一半干脆就是当地人在自己耍。多的是货船,运蔬菜、建材,乃至快递,DHL的黄色小艇,疾呼而过的红色急救船,再有就是水上巴士了。威尼斯岛上的公交全部是船,现在的家门口就是一站。办了卡,自由上下,船舱比陆上巴士宽敞些,一排能坐六七人。线路有十几条,甚至可以去往泻湖上许多偏僻的小岛。我最喜欢的是1号线,沿着大运河悠悠地跑,船舱外前排有临风的座椅,可远离船尾的马达声和船舱的闷憋。我常坐在最前头。常坐最前头的,还有上学下学的小孩子,背着书包拿着玩具,有学生青年,裹紧挡风大衣眯着眼,也偶尔有中年人,在暖阳下捧着一本书。船上大多是老年人,老年人大多缩在船舱里,或者在船尾无风的地方看报纸。本岛上的居民以老者为多,大多衣着讲究,彬彬有礼,去市场买条鱼也华装革履。人裹在衣服里,城市裹在建筑里。威尼斯的时尚与巴黎不同:以巴洛克为基调的变奏,在荣贵里面添一点俏皮的忧伤。
2 自己的狂欢节
来的那天晚上,低头拉箱子,最先得到的鲜明印象是关于一件您怎么也想不到的东西——地上的碎纸屑。那不是被某个绝望的初次失恋的人撕碎的情书或者中年夫妇吵架撕碎的婚约,而是密密麻麻像雪花一样一层一堆的尺寸规整的纸屑。它们是标准的圆形、菱形、五角星或四角星或被圆形切出的不规则半圆或弧形矩,都是彩色的,有红色绿色黄色橘色和紫色,大概比指甲盖还小一些,正好和天气最冷时北京的雪花片差不多大,片片分明地积在地上。但它们没有雪花那样浩荡,只是这里一团,那里一片,往往聚集在街道的中央,并屡屡在小巷里家家户户的门旁出现——就在台阶上,密密零落。仔细看时,有些深色的已经退了色,大部分都潮呼呼地贴在地面上,很少再被风吹起,被吹起来的也都归入街砖的缝隙里了。它们是我到达这里的时间点的最好证明——狂欢节的尾声。
满地都是欢呼的遗迹,它们尚未被海风完全卷走,而褪色的程度已经提示和记载了我来到威尼斯的时间——不多不少,正是新年之后31天又19个小时。威尼斯既是在海水通衢四方的大港,又像是在大山深处的乡镇,因为街道太窄,没有巴黎那样轰鸣的清洁车——连几片落叶都不放过要轰隆隆地吹走或吸干净,以至于跨年时的绚烂碎屑存留了这么久,仿佛狂欢就在昨天。可以想见我每天站在窗前看见的从水那边巷子里走过来转弯又过桥的银发阿公阿婆、背书包的小孩子、推着婴儿车的爸爸、叼着烟的青年男女——正是这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街坊邻居亲手摁下了那纸炮筒的末端,新年——噗!满地的色彩。大家也都任性不打扫,这些属于庆典的遗产就在街上躺着,飘到海里,漂到船脚。这个地方的狂欢终于有一次由当地人主宰。威尼斯终于等来了这样的光景。那天我去街角的酒馆吃一口Baccalà,老板娘从杂物间里翻了半天才找出POS机,沉吟了好久才想起来怎么用。酒馆里的街坊邻居们都大笑,好久没有来刷卡消费的异乡人了。而那些漂亮的船就被套上了雨罩在岸边寂寞着。
记得儿时那个本命年,妈妈给我买过一套打春牛的画册。这春牛,依古要在冬至后的第一个辰日取土在桑木骨架上塑成,约高四尺长 八尺,画四时八节三百六十五日十二时辰图纹。立春前一日,人到先农坛奉祀,然后用彩鞭鞭打,把“春牛”赶回县府,在大堂设酒果供奉。男女老少牵“牛”扶“犁”,唱栽秧歌,祈求丰年。画册上画的正是这个过程里的种种场景。我一直喜欢这个画册,就像一直喜欢陆游那首诗一样——“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虽然春社是立春后要再一月多,这中国古村也和海上共和国无甚相关,但我念来念去,总觉得立春的威尼斯就是这个恰切的感觉。
立春这些日也正是威尼斯的狂欢节嘉年华时期!虽然有疫情,没有天南海北的游客,周边的意大利人也不太活跃,可最后这几日,还是有各式各样的当地人服装秀。小孩子都穿得萌爆了,扮成小动物小恐龙小飞船小火焰,老年人们都穿成真正的巴洛克贵族,青年和中年大部分是塑料、彩色、搞怪和搞笑的,而今年重温黑死病的种种搞怖装也流行。大家熙熙攘攘地在阳光下花花绿绿地走着,小孩子四处继续撒着新年之后的彩纸屑,那场面不像是往日宣传里大家所描述的有中世纪宗教渊源的狂欢节,而像是一个小镇上的居民们用自己真诚鼓舞的方式在欢迎春天——如鱼上冰!终于来了,这春天。记得那天V和我说的,自从世界大战以来,威尼斯从未这般完整地属于自己过。
3 住下去
每天早上起来,看那些白头发、衣着精致考究的老头老太太,颤巍巍地过街,在码头上船,阳台上露出的头脑都是银行家的后代,手推车里贵族的晚年。窗前小运河上的船在晃动,所有的房屋、教堂、石板街道——二足所涉的一切都建在倒立于水中的木桩之上,他们都在晃动。这种晃动的幅度有点像钢笔尖在纸上的跃动。威尼斯大概是被文学家书写最多的城市。哦不,它不是城市。巴黎纽约那样大道通衢的地方才叫城市。威尼斯是一个巨大的客厅。全世界的人都在这里聚会。卧室,客厅,小巷,船舱,教堂,墓地,车站,餐馆,酒吧,从房间到房间,被长长的房间一样的巷子连通,被流觞曲水隔断,兜兜转转总还在这个客厅里。住下来,就看清了客厅里的那些威尼斯人。威尼斯人的心态是:我们在天的这边,天的另一边才是剩下的那全部世界——你们尽管来,但你们要想说上几句话,最好住下来。
住下来。让身体成为这里的一部分,这才算骑上了这只长着翅膀的狮子(威尼斯的城徽)。威尼斯也是一条鱼(卫星地图的直观,是那种胖胖的地中海金头鲷鱼)。从这里出发去游整个罗马帝国,向这里归来对这些游戏做个总结吧,不只是巴洛克、蒂齐亚诺或凤凰剧院,还有天主教皇、银行体系的诞生、雇佣军舰队和……语言:希腊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威尼斯方言。唐诗三百首(威尼斯有欧洲最大的汉语教学和汉学中心之一,Ca' Foscari的现任校长就是汉学家)——由语言,既而登上凌驾于语言的那种建构——诗歌、对话、调情或严肃文学。最近读的书里,《灵山》和《我的名字叫红》最爽,都是几天内一口气读完的。山带来了一种内容的可能性,所有漫游都指向我心中最渴求的主题,那么游记也不要再作游记写了。红是叙述结构的精彩绝伦,是对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最好的脚注。我现在明白阿城为什么在威尼斯当驻城作家写那么响亮的日记了。
住下来。人在哪里住?这就说到了乡土。一个能有自觉,觉察并热爱自己的故乡,乃至在各种意义上传承和守护着她的人是有福的。他的生命将敦厚如大树,不然就是漂泊,未被启蒙的无知,疲惫的挥霍——沦为无意义的美其名曰的旅游,再怎么包装、整顿、开发,复古或现代艺术,也缺了太多。虽然悟此,无奈,生在当世,常不如愿,不幸乡土不再,无法在原生意义上的故乡获得故乡感,仍尚有一种有恃于内无待于外的可能性——认清人生如世界的本质变动不居,一叶浮萍归大海,带着一种面朝故乡般的知觉、关怀、同情与同理,把自己生命中的一段时间投射在那时所在的那地,那么一朝一夕的扎根就是有力的。我们虽然不能扎在一处从头到尾铺陈一生,但尚可以借力于想象驰骋之术——于诗歌、文学、音乐或画,从观看那些如云如树的面孔到走入那些如溪如路的脚步,呼吸那里的气味就像把初恋留在那里,事实上,我们也只能以这种不断自新的心态去在漂泊中感受无处不在的“故乡”,因为我们每天从起床到安寝都在不断地被重新诞生出来,一次次诞生到这个不断刷新的世界上。故乡和他乡只在一念之间。有故事的地方就是故乡。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责编 :张婧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