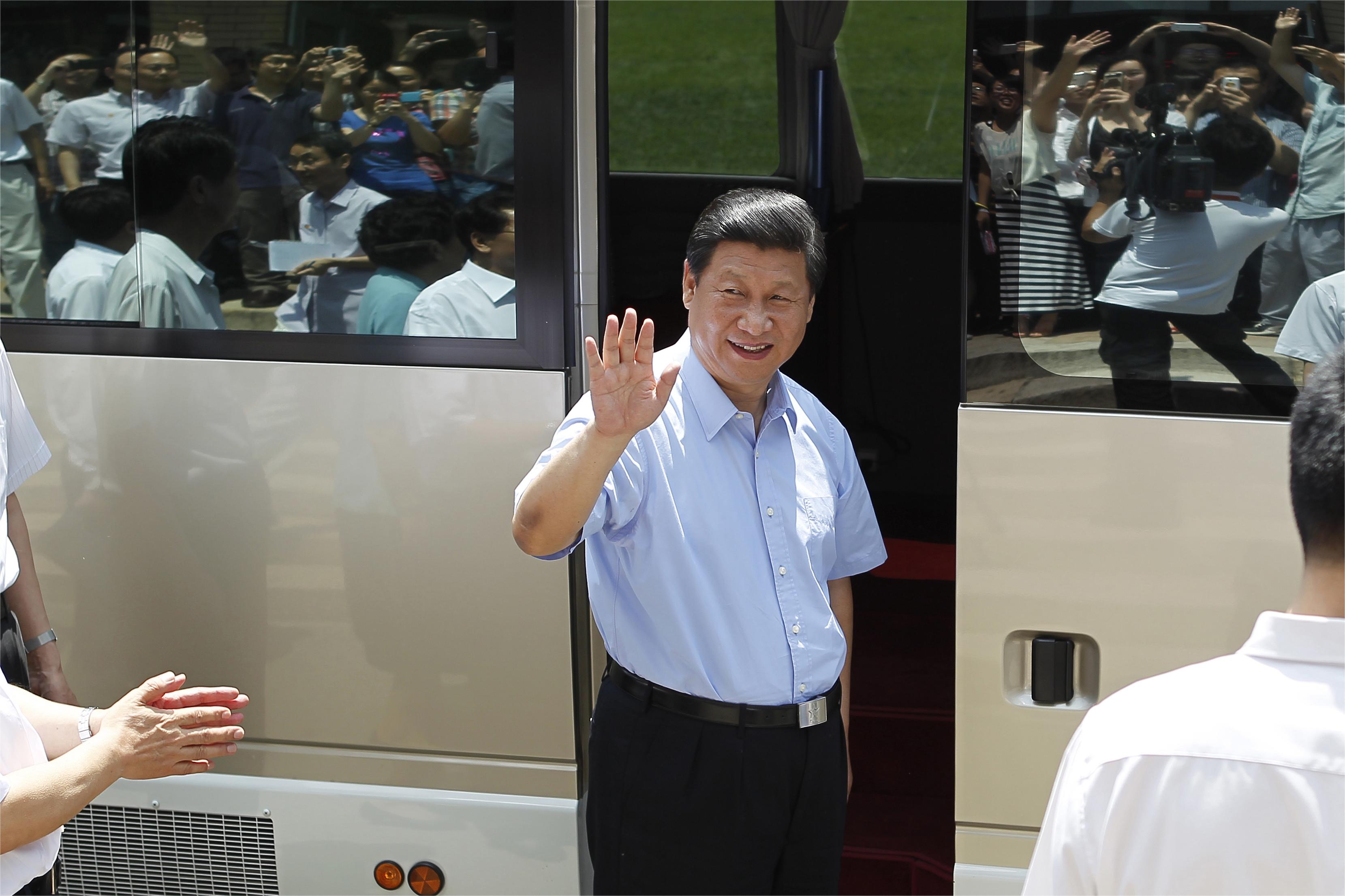塔,他

初识应县木塔,还是在初中的教科书上。那一篇《梁思成的故事》让我认识了梁思成和林徽因这对传奇伉俪,也认识了那座始建于辽宋年间的应州木塔。后到北京求学,偶然听到那句“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的谚语,应县木塔的模糊身影又浮现于脑海,我的内心有个声音告诉我,我需要做些什么,因为有种莫名的东西在召唤我。
那一年的深秋,我踏上北去大同的火车,盯着窗外,看景物飞快掠过,沉默无语,朝着应县木塔——那个曾经让梁思成激动得喘不过气的地方前进。下了火车,转乘汽车,我们越过雁门关,转入应县,车窗外突然出现的那一幕,深深刺激了我的神经。那一幕,我注定永生难忘。落日的余晖下,苍茫的大地上,一座沧桑古朴的木塔矗立于天地间,木塔结构与浑黄的塔基相互衬托,宛如饱经沧桑的老者,静静端坐,聆听风的声音,任他时间流逝,岁月雕琢,却依旧忘我陶醉。
当年梁思成是坐着骡车进入应县的,在距应县20公里外,他们一行人就看到了那座塔,他兴奋地写道:
“我到镇西五英里外时,正是落日时辰。前方几乎笔直的道路尽头,兀然间看见暗紫色天光下远远闪烁着的珍宝: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夕阳,掩映在远山之上。这座五层的宝塔从四周原野上拔地而起,高约二百英尺,天晴时分从二十英里外就能看到。由夕阳返照中见其闪烁,一直看到它成了剪影,那算是我对于这塔的拜见礼。我进入城垣时天色已黑。塔身如黑色巨人般笼罩全镇,但顶层南侧犹见一丝光亮,自一片漆黑中透出一个亮点。后来我发现,那是‘长明灯’,自九百年前日日夜夜地亮到如今。”
我感受到了他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激动,最后他只能用“绝对的Overwhelming(势不可挡)”来表达自己对于木塔之行的坚定决心。
下了车,站在塔下,向上仰望,那一刻,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但另一种感觉却立刻占据了我的大脑,就像是虔诚的信徒找到自己心中的圣地一般,那种喜悦与崇敬,来得太突然,让我都有些许的不理解。我,想试着去接近,去读懂这座塔。
登上木塔,踩在虽经过修缮却又显破碎的木质台阶上,不免有些胆怯。我注意到了留在木塔立柱和横梁上的弹孔,那是1926年军阀混战时留下来的,想必梁思成当时触摸着这些弹孔,内心一定是滴着血的。而在夹层的立柱上题着“拔地擎天四面云山拱玉柱,乘风步月万家烟火接云霄”更让这座始建于辽代的木塔彰显出雄浑的气势。站在塔顶,远眺四方,恒岳黯淡,干涸的桑干河道上,当年古老商队的驼铃怕是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历史上,民国时代曾对应县木塔进行过一次所谓的“修缮”。那一次,它被拆掉了原来各层间的泥夹墙和斜戗,换成了现在的门窗。这,发生在梁思成首测木塔之后。之后,他再来应县,木塔已失去了原来的光彩,他顿足捶胸,止不住仰天长叹。这次不合理的修缮,让木塔每层的结构整体性丧失,减弱了它的承载力和抗侧移能力,时间流逝,木塔已呈现些许的倾斜。
当年,梁思成为了保护应县木塔这一人类历史文化遗产而奔走,他与妻子林徽因协同其他建筑学者曾多次考察应县木塔。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他坚信世间有大美!而这,也是他当年会用诗意的语言向周总理描绘可能会消失的北京古都景象,全力反对拆除北京城墙的原因。 他曾感叹,“我是辽代的一块木头”,或许他也是“北京古城墙上的一块砖”,“奈良唐招提寺的一片瓦”。
应州塔的另一个名字,也就是它的正名,佛宫寺释迦塔,被我所知则是在图书馆偶然翻到的那本《中国建筑学史》,当年只是粗略读完,不过书中的内容我却记忆犹新。我不禁感叹,一个纯木建筑克服火灾、雷击、兵燹、虫蛀以及风吹雨淋,屹立1000年到现在,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地上建筑,应县木塔做到了。我突然明白了,应州塔矗立近千年,就像是在等待一个人,而那个人,或许就是梁思成,一个真正具有文化精神的人。他明白建筑没有国籍,它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财富。这个信念,让应县木塔真正为梁思成所读懂,而他的出现,也让应县木塔千百年来的矗立变为值得。
如今,梁思成作为一代建筑大家被载入历史,而那应县木塔,也依旧屹立在沧桑的古城墙边,千百年来,似乎只有一人真正读懂了它,那个人,便是他,梁思成。他是它的知己,或许也是唯一的知己。1936年梁思成再测应县木塔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去重登木塔,见见他的这位老朋友。陪伴它的,只有那雄浑孤寂的塞上大风吹动挂在檐角上的风铃,发出的千年回响。
那,也许是跨越历史,永恒的约定与坚守。而我,是读懂了它,还是只是个匆匆的过客,我不知道。突然起风了,被管理人员告知,该是下塔离开的时候了。
朔风怒处,风起云舒,我抬头望着雁北的天空……
责编 :黄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