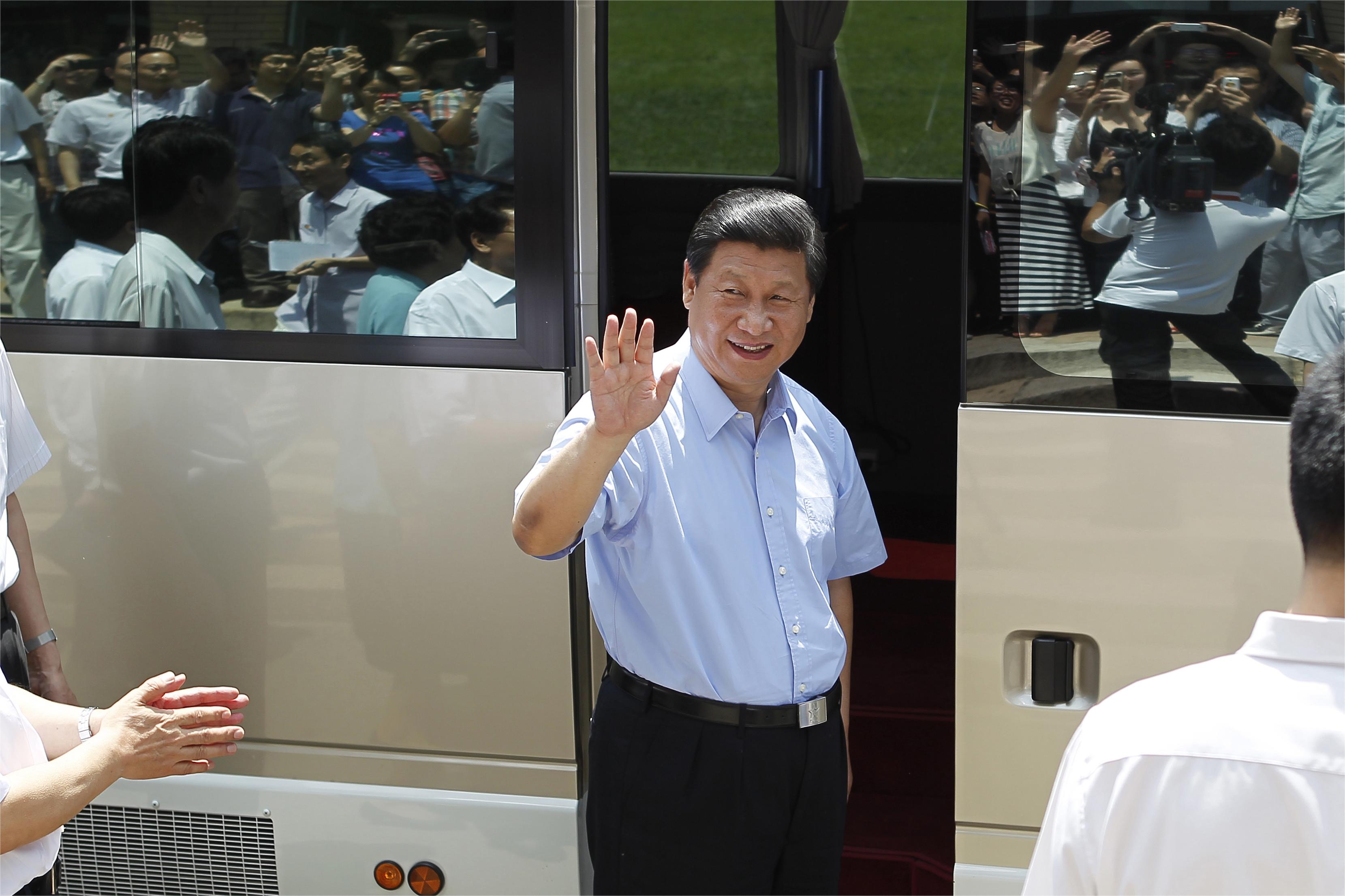白云回望合 ——读摘萧驰《诗与它的山河》

直到在玉泉路图书馆翻开这本书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多年来,我一直在期待这样一本书的出现。
在生活这凌乱的羁旅间我回望精神故乡,望中总是吟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免俗是容易理解的,可是你爱的是哪一番丘山呢?肯定不是干燥空旷、岩石狰狞的中美大裂谷,也不太可能是白雪皑皑荒凉雄壮的青藏高原。异域感里不会有乡愁。
乡愁指向的地方更像是王维笔下的终南山——白云青霭、阴晴众壑。这是中国的山水审美传统,是汉语诗精神的一部分内核。这种传统,以山水诗的形式,坚定而踏实地生长着,不仅吐纳出水墨画卷,亦滋养着诗客的具身生活,是而得以超然脱俗。
像回望白云一样,在人类整体文明的大关怀下,基于文本分析这种抒情传统的生成,乃至强调在地的山水对走入古人诗境之不可或缺,萧驰先生的皇皇巨著发展性地完成了这些任务。这本书不仅是关于诗歌的知识考古对比,更是对中国山水永恒现场的追溯与致敬。
连山接海隅
“最早认识自然山水之审美价值并持续进行书写,是中国文学令人瞩目的一项成就。关于自然风景的许多话语和观念都率先在诗中出现,而后方衍至绘画,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独特表达。”这种传统,滥觞于先秦,在诗经与楚辞中,都有绚丽的自然风物。但本书中关注的山水诗,指向一直持续的书写,其出现伴随着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大动荡、衣冠南渡、玄学清谈和地理志记的发展,指向一种对旅途风物的关怀,并进一步成熟于桃花源记——归园田居的山水栖居隐逸审美。通过现象与传统,作者中国山水精神的“生长”脉络,如同回望青山绵延。
西方研究中国山水画的学者苏立文说:谢灵运比仅仅为了欣赏景色而最早攀登阿尔卑斯山的彼得拉克早了近千年。远在文艺复兴之前,甚至也在以曹魏建国算起的魏晋南北朝之前,在欧洲罗马共和国和帝国之交的动荡时代,文学中已经出现了正面书写大自然的重要文本,如维吉尔的长诗《农事》。作者强调的是,与本书所关心的中国山水诗篇相比,维吉尔的长诗《农事》并非真正“基于个人身体经验”的创作,类似于柏拉图式的图景描述,并没有具体所指的地点。
而由谢灵运开创的山水书写传统能与汉赋辨分,一个重要不同即在于,这种山水诗的书写主要基于个人的身体经验——先是羁旅途中所见,进而是田园栖居生活。贝尔凯依据四项条件——一个或多个指涉“景观”的词汇,“景观”的文学表现,“景观”的绘画表现,“景观”的造园表现——认为历史上只有两种文明创造出“景观”文化,即中国南北朝时代及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而这两个跨越不同大陆的时代之间,已经相隔了何止千年。
倘若沿循贝尔凯两大文明传统的说法,应是中华文学与欧洲文学分别于公元前三世纪和公元前一世纪即开始了对大自然的正面书写,又皆因文化思想语境的改变一度失去活力。而“中国文学却在早于欧洲一千余年的东晋刘宋时代,发展出书写大自然的持续不辍之新传统”。因而,探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的关怀,这本书讨论的主题——中国古典山水诗书写——恰恰位于欧洲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之间的空白地带。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正是人类文学在这段期间“最重要的发展”。
难能可贵,得益于其海外学术背景,作者萧驰在书写中国传统诗学时,时刻带有面向全人类的文化关怀,并在建立论述时不断引入丰富的对比视角,把中国山水书写、中古山水美感这一主题放置在全球视野中探讨,可谓是茫茫连山,直接海隅。
阴晴众壑殊
“山水诗”这个语词,最早见于白居易《读谢灵运诗》(多么清晰的对话、呼应!)——“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白公忆谢公,清晰点明他“岂惟玩景物,亦欲摅心素”“往往即事中,未能忘兴谕”——中国诗人书写山水,自打开始就免不了“自传”成分,即书写其在山水中即刻的身体体验。
中国山水艺术许多话语和观念都率先在诗中出现,而后方衍至绘画——山水之美在先秦滥觞,被南朝晋宋诗人再度发现后,逐渐渗入了游览、送别、去离、闲情、行旅、登临、怀古、思亲、游仙和边塞等诸类题材。乃至在山水美感话语树的生长中结成一强烈的抒情传统:不能景语,何能情语?
本书中,自谢灵运被贬永嘉的永初三年迄至白居易于洛阳谢世的会昌六年这424年间,擅长风物书写的15位诗人次第登场。中国景观文化的根脉——“一元双极”的“山水”,清晰出现在开山诗人谢灵运的诗中,在鲍照那里又加入“天-地”来含涉云霞烟霭岚光风雨雪雾。作为氛围的风景,在谢脁的居停之望中形构,又成为“取景”的开端。而到了江淹与何逊那里,时象(时间出现在空间中的意象)成为景观主题,而且“风”与“景”中形成的光韵或氛围亦参与进来。视通万里之深思打开了天地框架,阴铿由此创造取景取境之上的张力和异质性。
“桃花源”是隐逸者空间现象学的一个寓言,而孟浩然和王维则分别体现了“桃花源”中“渔人”与“桃源中人”的不同视角视野。与孟浩然力图表现的空阔无边相反,在辋川的王维依身体存有句读的每个瞬间世界都是具足和独立的,仿佛只孤悬于当下的直接经验。“此处此刻最能体现由存在打开的空间知觉本质。”李太白的诗则彰显了“清”,也即一种人与感性事物“共存的场”,“诗人与水、空气此刻皆无以拥有本质,皆虚位以待和相互流通”;而杜甫笔下的夔州山水则是长安梦华的反衬,抒情史诗的意味令山水成为“山河”。韦应物所实践的则与杜甫完全不同,将身心完全融入山水的节律中,因而虚化了方域。
而元结和柳宗元的山水书写里,向往“不骛远不陵危”“可居可家”的人间山水的倾向,与谢灵运、李白等崇尚游历、新意的趣味截然相反,可谓延伸自王维辋川的栖居。韩愈则继承了李白凶险山水、柳宗元阴森山水,发挥了因流逐而生的“风土的乡愁”,又不乏其基于时代文化危机的异化感。白居易则试图突破对世界作整体化对待的观念,与南朝以来诗人居高俯瞰、立身于纷繁之外反观的模式不同,白居易令身体进入、参与、牵绕于此一场域中。
欲投人处宿
中国诗人的书写,免不了“自传”成分——传统诗论强调的“即目”“直寻”“现量”“情感须臾,不因追忆”云云,都将诗作视为诗人某种片段、瞬间性的自传。因而,山水在诗中,多为具体历史时空中的山水。这便指向了重温和追溯这种体验时一种无可替代的终极路径——找寻诗人对境作诗的那片山水,品味山水诗的在地性。
作者更向世人发起呼吁——中华山河不仅为古人吟咏的对象,亦是承载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广阔语境,一旦被横加破坏便再难复现,要注意保护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环境。
一方山水一经吟咏,即如典籍一样具有了传承斯文的意义,后代即可借这一处“山水”与前人“今古相接”。在古代著名诗人谢灵运、李白、王维等生活或流连的浙中剡水、皖南泾川和关中辋川,至今民间仍流传着关于他们的传说。某些村庄、河流和山岩,甚至由此而命名,如嵊县嶀浦的钓鱼潭、嵊州谢岩的康乐弹石、蓝田辋川的望亲坡、贵池里山江祖石的李白钓台,等等。这样的“山水”,已经是所存不多的古代宫殿、城郭、庙宇之外,能让后人真正触摸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物质遗存了。
然而,即便如此宝贵的遗存,近年已不当地遭到严重破坏。对六朝文学有兴趣的人,会知道流贯浙江新昌、嵊州和上虞的一条河流“剡溪”(下游称曹娥江),它汇集了山中许多清冽的溪流。这是王子猷雪夜访戴时舟行所经的河流,是李白的梦土,是中国乃至世界山水艺文的真正摇篮。据说20年前,此水依然清可见鱼,碧水青山之间,在在“清晖”游漾。然而这样一段承载无数文化记忆的美丽山水,却因两岸的国道和高速公路的修建者不舍得绕开而被破坏。蓝田辋川谷是另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这是昔日王维别业所在山谷,是王维读者神往的地方。但如今一条高速公路大桥已纵贯辋川谷,令人很难再去想象王维的诗境了。
所幸华夏山河仍然不乏守护者。为写作本书,作者在南北方进行过前后10次考察,接触到活跃在各地为搜集保护乡土文化而奔走的人们。最令人难忘的是年逾八旬的丁加达老人。他下放上虞农村期间,凭借《山居赋》与剡水周边各处地貌的对照,独立地发现了谢灵运《山居赋》所称“北山”庄园的真正位置。作者见到他时,他刚做完癌症手术,且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双眼视力已很差,只能靠呼吸机交谈。他以颤颤巍巍的手在纸上写下各种地名,并说很遗憾,他已不可能再去考察了。在翌日的考察中,他一再打电话给作者指点。此后不久,老人就去世了。
此书的出版,也是向所有华夏文化故土的守护者们表达敬意。毕竟,如同王维诗中最后切换回“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那般亲切静谧——“诗”的山河,正是围绕于“人”的山水。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责编 :张婧睿